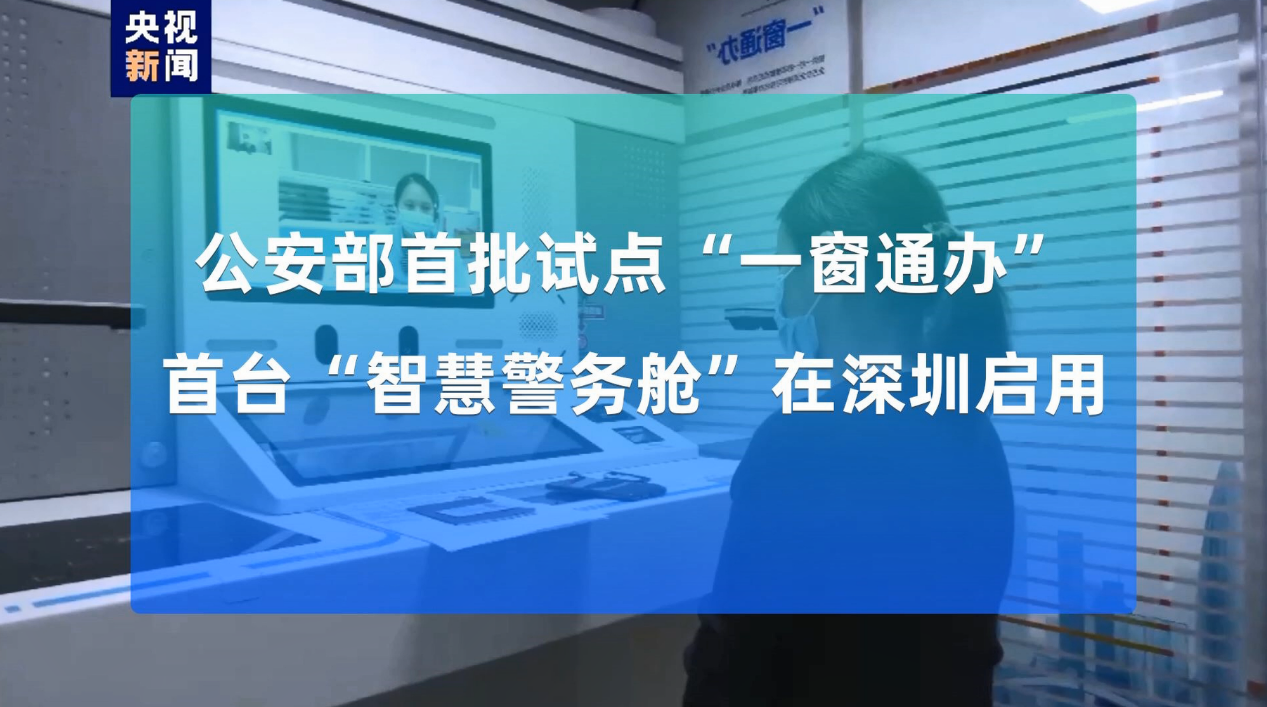蔡炳丁观点(蔡炳丁的博客)
伍跃
蔡老师远行之后的次日,刘志伟学兄传来了蔡老师在学而优书店检阅架上书籍的照片。看到那熟悉的背影和花白的头发,实在使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在遥望南天的同时,昔日在康乐园求学时的情景也涌上脑海。作为追忆,我再次展读了1982年夏天蔡老师寄来的一封信。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蔡鸿生老师在学而优书店
一
这封信一共三页,写在20×18的中山大学稿纸之上。我们在校期间,曾多次去生活区的商店买这种稿纸,因此非常熟悉。由于时隔多年,包括信封在内,保存得尚算完整,但已经泛黄,并开始有些发脆。
离开母校之后,我进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奉职于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后又东渡他乡,进入京都大学。毕业之后,又从京都到大阪任教。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内,我曾数次搬家,但是这封信却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始终将它带在身边,或许仅仅是出于保存文献的职业习惯或个人癖好。随着一次次的展读和自身年龄阅历的变化,我终于逐渐体会到这封信中蕴含着的精神力量!
三页纸中的一页是蔡老师用漂亮的俄文写下的学术著作书目。信中开出的四种著作中,我只查到了其中一种,就是下方写着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的那一种。我猜想,蔡老师或许会感到有些失望。
另外两页是信札本文,兹将主要部分过录于下:
伍跃同志:
七月六日信收悉。您入学虽仅半年,但已得到不少在中大所无的新认识,这就是一个新的起点。祝前程似锦。
谢谢您上次代查书目。其中《突厥文碑——中亚史料》一书,因北图已外借,今尚未能寓目,总有一天会借到的。随函附上俄文书目一份,烦到北图查查,如有入藏,请标明书号寄回。俄美公司是东印度公司式的殖民公司,我在这里只能读到零散史料(美国出版的档案,我已到国外设法购置),只知轮廓,未明细节。商务将于年内出版奥孔《俄美公司》一书,是三十年代的著作,也稍嫌旧了。
来信提及我那本小书,是十八年前的旧稿。记得当时一脱手,我就去“四清”了。如今再看,真有隔世之感。
北大有寅恪先生的传灯人,他的著作自然也会得到高度的评价。至于中大,不过是他老人家“棲身岭表”(他的话)的落脚地,曾留下足印,可有几人去踏勘?!我有幸听过他讲一年“元白诗证史”,至今仍在时时翻阅他的文集,带着凭吊的心情,不是在研究。《金明馆丛稿二编》中那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概括了王国维治学的三条经验,实际上也是寅老的现身说法。
君自岭南去,当知岭南事。号称“羊城”,特有洋味;号称“花城”,也特有花花世界的浮光。十三行在这里,十三陵不在这里。嗟夫,“食在广州”!近年虽也办起书市(当时您尚未毕业),但总不如花市热闹。
我们住老地方,诵《陋室铭》。据说,已列入搬家名单,何时才搬,由他去吧。
……。
问近好。并祝
健康
蔡鸿生
七月十九日
信函(书目页)
信函(第一页)
信函(第二页主要部分)
信封
二
我是1978年2月,自己用一根扁担挑着被褥等简单的行李,作为1977级的一员进入母校历史系的。1982年初毕业离校,转赴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离开母校之后,和蔡老师有过书信往返,其间多是奉命代老师在北京图书馆或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研究所需的外文学术著作。在网络工具尚未发达普及的1980年代,除了去图书馆翻查卡片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得到书目信息。当时有些图书馆对于某些特定类别的图书甚至不允许读者自行翻查卡片。相比之下,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基本上是完全公开的,实在是方便不少。当年,不仅是蔡老师,我还为其他师友略效过查找书目、代借代邮的微劳。从北大骑车一个小时进城去北京图书馆查书确实是一种知识的享受,我也由此学到了一些在教室未曾学到的东西。
我在给蔡老师的信中除了禀报查找书目的结果之外,还汇报了进入北大第一个学期的学习感想。蔡老师信中关于“寅恪先生的传灯人”和王国维的部分就是针对我的汇报而言。
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邓广铭先生主持下,强调史学基本功训练和通史教育。进校前,因为读过收录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知道陈寅恪先生称赞邓先生是“他日新宋学之建立”的“最有功之一人”。在史学基本功训练方面,邓先生特地请来杨伯峻先生为我们讲《论语》。在通史教育方面,要求学生在本人的主攻方向之外,必须选修其他断代史的课程。进校后第一个学期,我选修了王永兴先生的读书课,指定的教科书是白文的《大唐六典》。熟悉学术史的同行都知道,王先生是陈先生在清华大学最后一段时期的时期教学助手。王先生在讲解时有自己的精辟见解,并结合文献对《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相关部分进行解说。我自己觉得在这门课上既受到了阅读原典的基本训练,而且也开始萌发了研究制度史的想法。记得王先生要求严格,过录和标点史料的作业取百分制,如果出现文字或标点错误,一律各扣一分。我记忆中,似乎无人被扣至负数,大家都保住了颜面。此外,还选修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周先生自己在回忆录中说,在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曾经与同学一起去清华“偷听”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感觉好似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相信是“偷听”学到了真功夫,我自己感觉周先生将魏晋南北朝时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历史变化,分析得清清楚楚,尤其对南朝历史的说明把我们带入到如痴如醉的境域,确实是引人入胜!一起听讲的将无同学兄走出教室之后,连声叫好!现在来看,恰似听了一场王佩瑜拿手的老生戏,非常过瘾!周先生在讲课中,多次提及陈先生的见解,如北周、北齐等对日后隋唐制度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说明自己的观点。我已经想不起当时是怎样向蔡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感受的,估计是讲到上述两位先生在授课中对陈寅恪学说的阐述,故蔡老师在回信中除了勉励鞭策之外,还有关于“棲身岭表”的一番议论。
蔡老师在信中提到了《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篇文章也是当年北大诸位先生希望我们能够背诵的,至少是其中关于治学经验的部分。对于刚刚走入校门的我们来说,以较高的标准指示门径,实在是非常重要。这就是取法乎上,仅得为中的意思。蔡老师说,陈寅恪“概括了王国维治学的三条经验,实际上也是寅老自己的现身说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者也。陈寅恪在数十年之前指出的“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的论断,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蔡老师谦虚地称自己是“有意求法,无术传经”(《仰望陈寅恪》,稿竟说偈),但在我看来,老师传经有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实践着陈寅恪总结的上述治学方法。蔡老师在近代以前俄中关系史、以唐代粟特和突厥文化为中心的中外交流史、岭南地区佛教史、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域交流史,以及历史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领域留下的专著和论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始终贯穿着这些治学方法。
蔡老师信中对“可有几人去踏勘”陈寅恪留在岭南的“足印”的感慨,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只要是熟悉那一段历史,或者稍稍认真读过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以及黄萱先生回忆文章的人,就可以感知其中包蕴的意涵和力量!透过蔡老师使用的“?!”号,似乎可以看到掩在字面背后喷涌欲出的情感!而所有这些都转化为冷静求真的治学动力。信中虽然说自己是在“凭吊”,“不是在研究”,这些恰恰体现出季羡林先生称赞的“诚悫、纯朴”(《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序)。
三
蔡老师信中提到,在1982年夏天还在和家人“诵《陋室铭》”。此处的陋室是指母校东区的东二宿舍中一个小小的单人间,与我们居住的学生宿舍仅隔一条小路。那幢长方形的红砖楼房是岭南大学时期的建筑,东南西各有一个出入口,恍惚记得南面入口上方还隐约可见“某某堂”字样。因年久失修,乏人打理,楼顶的绿色琉璃瓦之间长满茅草,称之为茅舍亦不为过。加上广州四季湿润,校园植被葱郁,真有些“苔痕上绿阶,草色入帘青”的模样。我不知道该建筑原来的用途,我们在校时被用来作教工宿舍。那个楼房的建筑格局是所谓的筒子楼,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房间。过道两侧堆满了各种生活用具,各家各户炒菜煮饭就在自己房门外的过道上,可谓一家爆炒,全楼闻香。楼内弥漫的气味可以说是菜市场与大排档的大汇集。长年的烟熏火燎,致使无从辨认过道墙壁原来的颜色。广州夏季炎热,昼夜的室外气温常在正常体温之上。当年没有电风扇,更不知空调为何物。其实,夜晚若能有电照明已经堪称是相当奢侈。我记得那个年代挑灯夜读的灯几乎都是煤油灯,买不到煤油的时候就用蜡烛“然脂”读书。我到母校读书前住在北京四合院的平房,对楼房=洋房有着莫名其妙的憧憬。不过,看到东二宿舍内部的情况时,我不禁连想到明清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穷书生”和“穷塾师”,怎么也不能和“华南第一学府”的“大学教员”划上等号。
蔡老师的房间是一楼最西面紧靠入口的一间,我印象中房间面积比我们七个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大不了多少,堪称斗室。老师和我们坐在一起,真是到了“促膝”的程度。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生活用具已经占去了大半空间,一张小小书桌几乎和我们学生宿舍的桌子差不多大小,一个谈不上起眼的书架,在桌边和墙边放着一些书籍,其中有不少俄文的学术著作。墙上有用晾衣服的夹子夹住的一些纸张,不知是资料文稿,还是学生作业。这里虽无“丝竹之乱耳”,但是各种生活噪音却是不请自入,至于“案牍之劳形”则是确确实实的写照。主人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精神,在陋室中“调素琴,阅金经”。在我等勉强可算“白丁”的后生小子之外,一定有不少“鸿儒”曾经造访。我想,“鸿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当年应和蔡老师一样,都是以积极求进的心态,生活在这种心目中“何陋之有”的陋室之中。每每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刻印在脑海中的这一幕不仅是对刘禹锡那篇名文的现实注解,更凸显了那一代中国学人的强韧与坚卓!
我记不得最初因为什么事和同学一起去了蔡老师的斗室,总之从那以后就常常去求教打搅,往往一聊就到了第二天凌晨。学术话题之外,我们还在一起关心过容志行领衔的中国足球队能否冲出亚洲。当时,蔡老师多数时间一个人生活。远在湖南的师母前来探亲时,就坐在一边静听。有时夜深之后,还为我们准备一些简单的夜宵。在我的记忆中,蔡老师和师母从来没有对我们下过“逐客令”。现在想来,当年的我等实在是乳臭未干,不谙世事,全然不顾及老师的私人空间和备课工作,甚至也根本没有考虑到老师的经济负担——那时的老师们大多收入微薄。在一次次夜语长谈中,最最打动人心还是蔡老师言谈中的睿智与渊博,运用自如的古典与今典。恰如刘志伟学兄所说,东二宿舍的那间陋室已经成为我们的共通记忆。
2002年8月9日 于康乐园东南区1号前(姜伯勤老师摄)
四
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蔡老师的生活可称“清贫”。我印象中,最初见到蔡老师是在历史系召开的师生见面会。会议主持人对所有教员均称为“老师”,没有使用教授一类的称谓。蔡老师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脸色不好,加上微微的驼背,看上去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以为是很快就要停年退休的“教授”,至少也是“副教授”。当某位消息灵通的同学从教工名簿上发现快要“停年退休”的这位老师不过还是一名助教(好像在我们毕业前升到了讲师),于是宿舍中不免有过一番月旦春秋。
我原来印象中的大学教授,或是用包袱皮抱来一堆线装书,或是从考究的皮包中拿出一本讲义。但是,蔡老师的课彻底颠覆了我的固有观念。最初来给我们上一年级的世界通史课时,蔡老师只带一张纸,这就已经让我大开眼界。更神秘的是,老师有时还带来一个布口袋。这个口袋有时是空的,有时好像装着什么。最初总也搞不清是用来做什么的,因为蔡老师讲课虽然留下思考题,但是从来不收作业,故这个口袋不可能是用来装作业的。后来有同学在生活区的粮食店发现蔡老师用那个口袋买米,于是揭开了大家的谜团。我自己也多次看到蔡老师背着米往返在宿舍——教室——生活区的身影。那个背影与刘志伟学兄传来的蔡老师在学而优书店看书的那张背景虽然相距数十年,但在我脑海中完完全全地重合在一起!
应该说,这种为了学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上巨大压力的情况应该是上一代不少学者的共通体验。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在相当困难,“只能读到零散史料”,甚至享受电灯照明都成为奢侈的年代付出了现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一座座学术上的高峰。每念至此,不免汗颜!
蔡老师思维深邃,尤善融汇贯通。他在信中对“羊城”与“花城”,“十三陵”与“十三行”的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在讲课时也是这样。离开母校时,我带走了全部的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蔡老师讲授世界通史古代史部分和俄中关系史时的听课笔记了。蔡老师讲课印有讲义,但是每次讲的内容几乎都是讲义上没有的,即便有也不过是短短几个字而已。蔡老师讲课仅带纸或卡片——这种做法在我目下服务的学校恐怕要被点名通报,进入教室之后先将前面提到的米袋放在门边的角落,然后开讲。开讲时,蔡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今天的题目,然后就是以沉稳的语调一气呵成,间中看一下带来的纸张或卡片,遇到重要的名词另外写有板书。这种讲授方法对于我这个刚刚离开高中,作笔记只会照抄黑板上板书的人可谓是相当痛苦。蔡老师讲课十分生动,除了说明重要历史事件的经过和历史人物之外,用了很多时间进行分析,甚至与中国古代史中的某些史实进行对比。尤其感到新鲜的是,蔡老师用“人类在童年期的近似性”说明古代东西方世界中一些看似相近的历史现象,使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也开始感觉到学习历史,尤其是作为学术的历史学,虽然需要把握年代、史实、人物等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发覆”,要学会看懂读透历史文献传递的讯息。
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那门课的考试。当时,在我的理解中,考试都是闭卷,而且教员不停地在教室内走来走去,履行监考的职责。但是,蔡老师那门课考试时,记得只有一道问答题,而且允许我们参考讲义。考试开始,他本人在黑板上大书考题之后(我印象中好像是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问题),就离开了教室,待到考试快要结束,他才又悄悄地走进来。而且,当时的教室中即便监考老师不在,同学们都是专心致志地解题,没有人交头接耳,更无人借机取巧。说老实话,我个人至今依然十分怀念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前期校园中的学术氛围。
我们在校期间,已经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上课和其他场合已经没有必要动辄马恩列斯毛。也许是顾及我们曾经受到过的教育,蔡老师常常用我们这一代十分熟悉的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主张,鼓励我们广泛阅读,并在课程中和闲谈时介绍了不少欧洲的近代思想家。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多年之后,当我读到他引用海涅对路德的评价,看到《仰望陈寅恪》引言中“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黑格尔)时,依然觉得好像身处昨天的教室或昨晚的陋室。从蔡老师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熟悉“异族之故书”。以后,当我接触朝鲜史籍和翻译夫马进关于朝鲜燕行录的论述时,就想起蔡老师早在上课时已经利用来华朝鲜使节的燕行录,描述过京城玉河桥边俄罗斯馆的情况。除此之外,蔡老师对“吾国之旧籍”也十分熟悉,诗文佛经,可谓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我相信,其中有母校历史系大师云集时代,尤其是在金明馆的薰陶,更多地一定是源自他本人在陋室中的苦“阅金经”。
蔡老师信中说,自己在岭南“只能读到零散史料”。我初初读到时感觉语中透露出一丝苍凉与无奈。以后则深深地感到,在这些平易文字的背后有着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力量!也是对我们的勉励与鞭策。以远居南国之身,爬梳北地乃至西北中亚的史料,在今天或许已经是稀松平常,在那个年代实属不易。我自己曾经设想,如果蔡老师在精力旺盛之年不是去“英德留学”(蔡老师原话),如果……的话,一定会有一部全面论述近代以前俄中关系史的巨著,该书构成老师名山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引后人继续登攀。
信中提到的“那本小书”是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的《罗马晚期奴隶起义》,我购入时的定价是人民币零点一八元。按照蔡老师的说明,该书脱稿于出版前十八年,即1963年。此时的蔡老师刚到而立之年。次年,四清运动开始,以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了。蔡老师看到该书出版时已经是接近知天命之年。进入还历之年以后,蔡老师多年的积累陆续结实,其中《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尼姑谭》(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教出版社,1997)和《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完成于六十到六十九岁,《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学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完成于七十岁以后,在2018年更以八十五岁高龄出版了《广州海事录: 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商务印书馆)。我没有仔细计算过蔡老师全部著述的字数,但仅就管见所及,上述这些发表于六十岁之后的著作很可能占一生著述的绝大部分。蔡老师身体力行,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老来事业更辉煌”。
工作之后,我又数次晋谒。此时,蔡老师已经搬入了新的教工宿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2002年暑假期间的8月9日,承蒙老师和师母招待家庭便饭之后,蔡老师提议散步去康乐园东南区一号——陈寅恪故居。好像是蔡老师打了电话,姜伯勤老师也过来一同前往。途中听蔡老师讲述当年修读“元白诗证史”的情景,听他讲助教黄萱——他在“英德留学”时的“战友”,讲到黄萱的夫君周寿恺,讲到蒋天枢先生为保存、整理老师著作付出的辛劳等等。虽然有些在蔡老师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已经读过,没有什么“爆料”可言,但听到那带有体温和情感的娓娓叙述,还是令人情难自禁。
记得最后一次晋见是2012年3月14日在永芳堂一楼,获赠老师的《读史求识录》。返程途中,读到老师关于“学者最难得的气质:甘于寂寞”的论述。在老师的说明中,寂寞是一种定力,是一种他人难及的精神境界。我想,这正是老师自己多年的经验之谈,老师就是在寂寞中读史,在读史中求识,在求识中为我们留下了必须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永远怀念蔡鸿生老师!
伍跃
2021年2月17日草于乐音寺
同年4月5日再订,时值清明后一日
关键词: